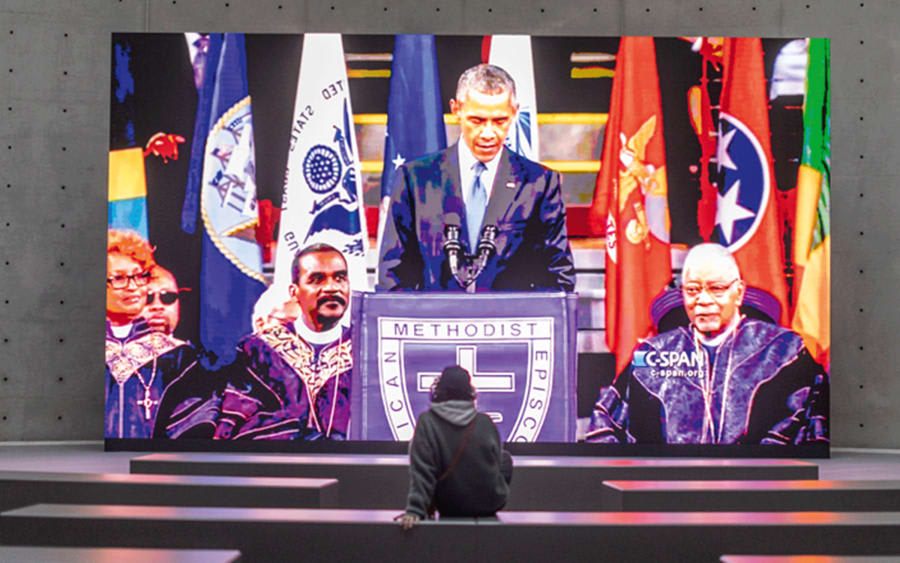藝術家萊昂納多.德魯(Leonardo Drew)的工作室位於布魯克林Cypress Hills的一間改建車庫內,瀰漫著一種看似混亂但井然有序的氛圍。該街區遠離布魯克林的潮流中心,鄰里大多講西班牙文。在前方的工作區,一名助手正將那些經過鋸切、火燒與風乾的木屑碎片黏貼到凹凸不平的黑色棉塊上。這種對材料的實驗與運用,正是德魯標誌性的創作手法:抽象但卻令人著迷的手工創作。工作室後方,充滿生氣的雜亂景象映入眼簾:木板和面板堆疊如山,散落著成堆的油漆碎屑、鏡面殘片、桶裝牆漆以及色彩樣本。一張由木板拼接而成、如窗簾般起伏的薄片懸垂著,走廊則堆放著一捆捆被白布包裹的神秘物件。德魯在其間從容穿梭。
天花板一隅,高懸掛著德魯口中的「爆炸性」作品之一。德魯所有的創作均以數字命名,按序編號。這些作品往往轉瞬即逝——一旦回到工作室,它們隨時可能被拆解,其構件被重新利用,融入到下一次的全新構想中。此刻,那些焦黑木塊如鴉群般密集棲息於天花板夾角,又沿著牆面四散開來。「這些雕塑就像是在空間中作畫,」德魯解釋道:「它們以獨特的方式延伸發展,在虛空中刻畫出自己的存在軌跡。」
以編號而非命名的方式標記作品,任其承受解構與重組的過程,這正展現了創作者與形式之間的一場獨特共舞——在這支舞蹈中,材料始終掌握著主導權。「我認為最大的饋贈,就是將自己置於必須破繭而出、或發掘下一個可能情境的處境中。」德魯如此詮釋。德魯表示:「以數字命名作品,能讓我作為創作者與作品保持距離,也讓觀者能夠擁有完整而純粹的觀看體驗,而非由我來定義他們所看到的作品。」
現年64歲的德魯精力充沛,近年來備受矚目,並身兼一系列大型委約項目。目前,他在南倫敦畫廊(South London Gallery)主展廳呈獻了一件巨型裝置作品——觀眾可穿梭其間,彷彿步入一場定格的木片瀑布,那些被塗以色彩的木質碎片從牆體中噴涌而出,懸浮於半空。
德魯在多年藝術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與哲學觀,其1988年創作的《數字8》(Number 8)被視為其藝術生涯的轉捩點。這件作品完成於他從紐約庫伯高等藝術聯合學院(Cooper Union)畢業三年後,次年在紐約藝廊Kenkeleba House的群展「Pillar to Post」中亮相。作品整體呈現黑褐色調,安裝於牆面之上,繩索、獸骨殘骸、皮毛、羽毛與木板交織捆綁,營造出沉重陰鬱的氛圍。 德魯也因此被歸入幾條彼此交匯的藝術譜系——后極簡主義、拼貼裝置、非裔美國人文化傳統等,並確立了自己在作品規模與質感上的長期探索。然而,德魯的材料語言始終處於流動之中。 紙張、顏料、沙子、鏽蝕金屬、樹枝與木梁、鏡子、織物、原棉、陶瓷等,皆以不同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留下印記。以原棉為例,這種材料曾經在1990年代的作品中扮演關鍵角色,如今已悄然退場。其中一個德魯廣為人知的創作軼事:他曾經推著巨型棉綑穿梭曼哈頓下城,前往其恩師,畫家傑克.惠頓(Jack Whitten)的工作室。如今,這些棉料早已變為難以辨認的創作用料,無法再以簡單的話語詮釋。
對德魯而言,一旦作品變得明晰——無論是對觀眾,還是對他自己——便意味著是時候抽身而退了。他解釋道:「我的思維方式與眾不同。」然而,有時這也意味著主動放棄唾手可得的機會。這種傾向早在德魯少年時期便已顯現。那時,他是一位繪畫天才,尤其擅長繪製超級英雄人物,甚至得到了漫威與DC漫畫的青睞,這對於一位成長於康乃狄克州橋港(Bridgeport)公共住房、出身工人階級的孩子而言,已是難得的機遇。但當他在藝術書籍中看到傑克遜.波洛克(Jackson Pollock)的作品時,德魯意識到,眼前還有更有趣的道路等著他去探索。
今天,德魯的作品已被諸多重量級機構永久收藏,其中包括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(Museum of Modern Art)、古根漢博物館(Solomon R. Guggenheim Museum)、英國泰特美術館(Tate)等。然而,即便聲名鵲起,他本人卻依然保持著低調神秘,時常隱匿於公眾視野之外,動輒數周乃至數月,前往他在德州佔地十英畝的藝術駐地——那裡散佈著他親自建立的四座工作室。他常常獨自創作,從土地與天空中汲取靈感。「在那裡,我能回歸本真,找到真正的自我。」他說,「能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,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美好。」
德魯的「爆炸性」創作階段始於六年前,當時他受邀在紐約麥迪遜廣場公園(Madison Square Park)完成首個戶外公眾藝術委約項目。作品中,色彩繽紛的金屬沙質馬賽克附上鋁片,像一片片覆上草坪的織毯,以木質方塊構建出微縮城市景觀,錯落有序地排列。兩座高度近五米的塔樓聳立其間,由數千片彩繪膠合板構築而成,宛如一對現代廟宇,通過尺度上的變奏,回應曼哈頓公園與周邊摩天大樓林立的都市景觀。
在工作室中,德魯放任那些塗彩的木質碎片紛飛四散,彷彿被一種反沖力驅動,解構都市與抽象主義的秩序網路,並釋放其中蘊含的元素。此前幾年,他曾多次造訪中國東部的瓷都景德鎮。在那裡,他嘗試將施釉陶瓷打碎,再置於窯中燒制,使其在窯變中隨機重組,形成不可預測的紋理。這段經歷啟發他創作出新的木片雕塑,在動勢與色調層次上類比陶瓷碎片的張力與變化。
自2019年在紐約勒隆畫廊(Galerie Lelong)展出如蜜蜂傾巢般破牆而出的彩繪木片裝置《數字215》(Number 215),德魯的「爆炸性」作品便持續在沉浸感與規模上拓展。無論是在勒隆畫廊、Goodman藝廊的展覽,還是在各大機構的委約項目中,這些作品都不斷進化。對德魯而言,這一過程既是富有象徵意味的探索,也是一種視覺建構的實踐,創作「指令」皆源自材料本身。「我並非預先構想一切。」他說,「這更像是一場試驗,試圖將動能本身引入作品之中。」他補充道:「這些作品其實會調動你的身體,或許觀眾也在參與創作。」
這一方法的確卓有成效。在南倫敦畫廊的新作中,德魯解構並重組了他近期多個裝置的部分元素——包括2021年在康乃狄克州哈特福的沃茲沃思雅典娜藝術館(Wadsworth Atheneum)與2023年英國約克郡雕塑公園(Yorkshire Sculpture Park)展出的項目,同時又增添了更多木屑碎片,這些碎片均在工作室內由市售木材切割、上色並刻意做舊而成。如此龐大的裝置搭建必然是一項團隊協作工程,德魯將其比作一場集體即興演奏——如同自由爵士。「就像是一場爆炸,各種碎片四處飛濺。」他說,「所有的材料都已鋪陳開來,沒有對錯之分。但一旦你把它們安置到位,就無法再做改動。而我,作為藝術家,必須相信隨機的創作結果——就像颶風會隨意拋擲一切。」
確實,德魯時常將自己與材料的關係形容為「隨物運化」。這種理念使他拒絕使用承載過多歷史能量的現成物,轉而親手進行切割、上色、氧化與乾燥——將這些過程全部融入創作構圖。正如他所言,這種方法幫助他在混沌世界中尋找秩序。「這實則是一種生命哲學。」他說道,這種哲學讓他能篩選世俗瑣碎,追求「宇宙性的領悟」。
在這個政治分裂的時代,德魯的作品呈現出另一種形式的散射——彷彿先了解危機的狀態,進而超越它。「我沒有答案。」他說,「我只能信任你,當你凝視這些作品時,會告訴我你從中看見了什麼。這種信任的基礎,源於我們共同經歷的旅程——一段集體的旅程——我們都在奮力抵達某處。」
萊昂納多.德魯由Goodman藝廊(約翰尼斯堡、開普敦、倫敦)、勒隆畫廊(巴黎、紐約)及Anthony Meier Fine Arts(加州米爾谷)代理。
「Leonardo Drew:Ubiquity II」
南倫敦畫廊(South London Gallery)
展期至2025年9月7日
Siddhartha Mitter是一位自由藝術記者與評論家,主要為《紐約時報》撰稿。
所有照片由Tonje Thilesen為巴塞爾藝術展拍攝
2025年6月26日